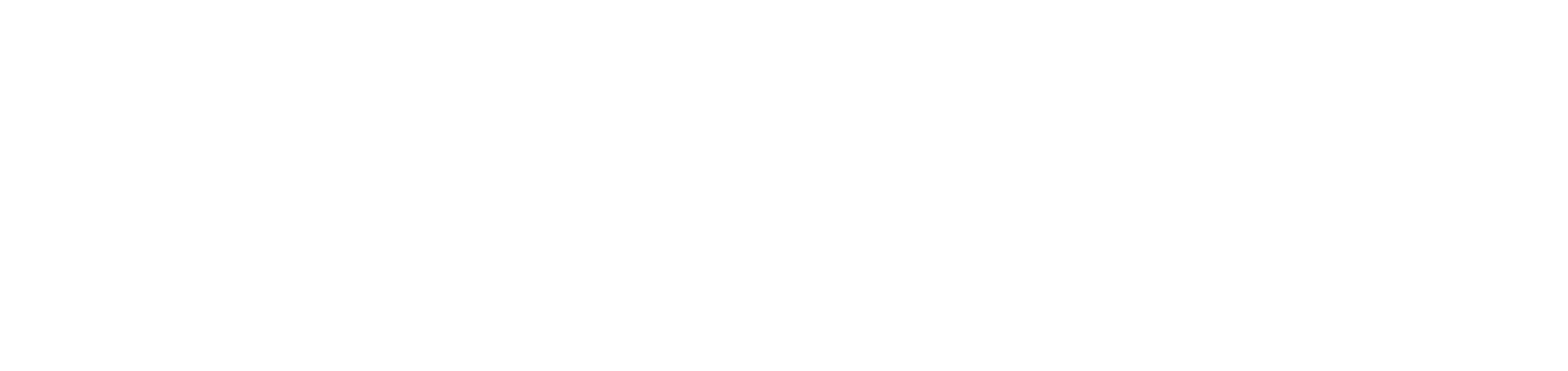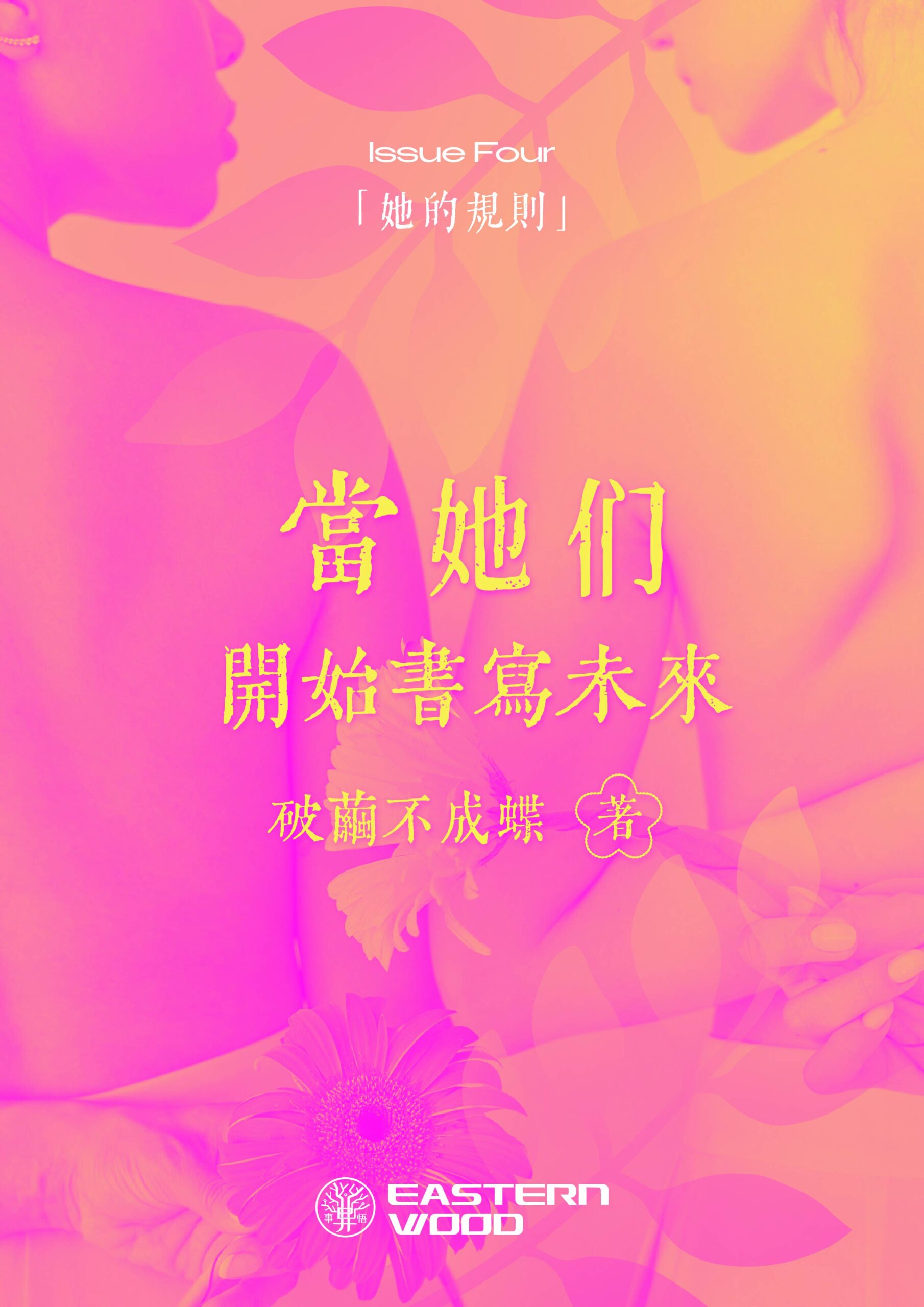全文约10600字,预计阅读时间21分钟
正文:
当“科幻”与“女性主义”这两个关键词同时出现,你会想到什么?
时光倒流回18世纪末,曾有一对传奇母女,为它们写下了最初的注脚。
1790年,正值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英国思想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凭借作品《人权辩护》一举成名。1792年,她又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女权辩护》,其中写道:“我主张女性权利的主要论据,建立在一个简单原则之上……真理必须适用于所有人,否则它就失去了在普遍实践中的意义。”
五年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因产后感染导致的败血症去世。她生下的女儿取了与她相同的名字,后来与诗人雪莱结婚——这就是玛丽·雪莱。
1816年,玛丽·雪莱夫妇与朋友们在日内瓦湖度假。连绵的阴雨天把他们困在室内,拜伦便提议每人写一个灵异故事打发时间。事后,只有玛丽·雪莱的作品真正成型。
据玛丽回忆,那时丈夫与拜伦常侃侃而谈,有一次讨论了各种学说,包括传闻中达尔文尝试创造生命的实验。这启发了她在夜晚“脑海里涌现出一连串的形象”,半梦半醒之中,她看见了“一个面色苍白、专攻邪术的学生跪在一具已组合好的人体旁边”。她被吓坏了,同时意识到,这就是她想要的鬼故事。这一恐怖想象被扩写成长篇小说,并在1818年出版为《弗兰肯斯坦》一书。小说中,科学家造出了一个怪物,它似人却又非人,不被社会接纳,最终向创造者发起了复仇。《弗兰肯斯坦》将科学与幻想元素结合起来,超前地探讨了科学伦理,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此外,玛丽还创作了多部科幻作品,其中于1826年首次出版的《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是末世科幻的鼻祖。小说中,一场瘟疫席卷21世纪的地球,人类濒临灭绝,文明崩溃。她以浪漫主义的笔调写出无尽的孤独,也做出了警示性的预言。
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两位女士血脉相连。而一旦将她们联系起来,就不难发现,她们的创作在冥冥之中形成了奇妙的呼应。
对于未来,母亲从人权角度出发,乐观畅想了一个人人平等的文明社会:“卢梭力证原始的一切都是好的;很多其他人认为现在的一切都是好的;而我则认为一切在未来都会好的。”
女儿则抱以更加冷静和警觉的态度,质询道:科学技术会把人类的命运引领至何处?当人类掌握了与自身能力不匹配的力量,我们是否能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在对未来的想象与建构上,女性主义与科幻文学有着深刻的共鸣,因此二者天然契合。女性需要科幻,而科幻也需要女性。
但为什么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把“女性科幻”单独拎出来谈论?
这还要从女性在文学、科学界的双重困境说起。
一、她们不是不存在,只是没有被看见
女性真正在普遍意义上获得教育权,不过是近百年的事情。
早期针对女性的教育,主要目的是把她们培养为贤妻良母。直到半个多世纪前,世界顶尖高校的女学生仍常被视为是“为了嫁人”才来求学的。正如英国最早的女性文学《简·爱》所描写的,家庭教师是18世纪英国女性能够从事的极少数职业之一,但她们的地位往往与佣人无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辞去家庭教师的工作、靠写作养活自己,这在18世纪末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当时几乎没有女性能做到。
在漫长的历史中,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的女性至少要集齐家境优渥、父母开明等条件,才不至于被埋没;即使她们能够幸运地崭露头角,也会面临重重阻碍。许多出类拔萃的女作家也曾经突破传统束缚,但她们的成就却总是或被低估,或根本不为人所知。《弗兰肯斯坦》在投稿过程中就曾屡遭拒绝,最终玛丽以匿名方式投稿,并由珀西作序,这部小说才得以出版。
在玛丽·雪莱之后长达百年的时间里,科幻文学处于一种萌芽状态,除少数著名作家外,写作者往往对科学理论不求甚解,多数在艺术手法上也略显粗糙。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美国男科幻编辑雨果·根斯巴克和约翰·坎贝尔培养了一批杰出的科幻作家,许多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都诞生于该时期。在这一阶段,科幻创作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也因此被后人誉为科幻文学的“黄金时代”。
乔安娜·拉斯是最早挑战这一状况的女作家之一。1968年,她凭借《在天堂野餐》(Picnic on Paradise)初露锋芒,此后陆续发表了多部科幻作品。当时,科幻文学界几乎被男性垄断。尽管乔安娜在女性主义科幻领域备受推崇,但她从未受到科幻文学界或是美国主流文学的认可和接纳。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乔安娜《如何抑止女性写作》的写照。这部文学批评作品出版于1983年,援引的例证跨越了几个世纪,涉及文学、戏剧、绘画等领域,鞭辟入里地揭示了西方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围剿”——人们或出于无知,或出于恶意,常常忽视、贬低女作家的成就,打压女作家的创作热情。
在书中,乔安娜·拉斯总结了十一种“抑止”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她不该写”“她写的算不上真正的艺术”“她的创作接受了别人的帮助”“她没有女人味,不够贤良”“她超越了自身性别的弱点,写得像男人一样好”……她还发现,不论是文选还是大学的阅读书目,女作家总是作为边缘群体起到点缀作用,“总有足够的女作家凑足那个5%,却又永远不会多到超过8%”。
乔安娜·拉斯本人也曾不够自信。她回忆,上大学时,她深信“自己的创作显然不属于‘伟大的文学’”。幸好,她还是写了。她说:“我有意决定去写没人懂的东西。所以,我就写了伪装成幻想小说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就是科幻小说。”
无论题材如何,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女作家都曾匿名或以男性的身份出版作品。乔安娜也遭到过拒绝,一位出版社编辑给出的拒稿理由是“女科幻小说家的书不好卖”。从19世纪的乔治·艾略特、艾米莉·勃朗特,到20世纪的莉莉丝·洛林(Lilith Lorraine)、小詹姆斯·提普垂,再到以中性名字发表《哈利·波特》的J.K.罗琳……用莉莉丝·洛林的话说,“如果编辑和出版商知道我是女性,他们不会给我超过现在一半的报酬”。
除此之外,女科幻作家比其他类型的作家还要多一重阻碍:自黄金时代形成的普遍认知是,科幻写作需要相应的科学理论知识,而科学长久以来都不是刻板印象中女性所擅长的领域。“女人不会写科幻”这样的观点从而大行其道。
但是,如果她们没有机会储备足够的科学知识,又该如何写出科幻小说?如果社会否认她们拥有掌握科学知识的能力,她们写出的科幻小说又该如何获得认可?
科学领域从不乏隐匿于历史的伟大女性,这便是著名的“玛蒂尔达效应”。人们倾向于忽视女性的成就,甚至将其归功于她们身边的男性,最终,她们湮没在了历史中。
然而,女性的经历本身就包含了许多文学母题,每一个“她”的故事都可能启发一部科幻小说。
比如,直到今天,程序员仍是男性主导的职业,但世界上第一位程序员却是女性——数学家阿达·洛芙莱斯,她为最早的计算机雏形巴贝奇差分机编写了第一个程序。在计算机尚不发达的20世纪50年代,NASA雇佣了大量黑人妇女担任“人肉计算机”,其中凯瑟琳·约翰逊脱颖而出,成为计算各种重要航空轨道参数的关键角色。她从未放弃在报告中署上自己的名字,凭实力突破了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壁垒。2019年,以此为灵感、讲述女科学家打破性别壁垒的小说《计算群星》获得星云奖。
1974年,病毒学家黄诗厚等人对生物学女博士的职业困境发表了首个数据研究。研究表明,女性的晋升速度普遍慢于男性,且每一阶段的薪酬也更低,收入差距随职业地位提高而扩大。当时,女性平均只能挣到相当于同学历男性68%水平的薪资。几年后,一个名叫琼·丝隆采乌斯基的大学生从生物学系毕业,1984年起,她在美国名校凯尼恩学院教授生物学8。1986年,她的科幻小说《入海之门》出版,书中构建了一个位于海洋星球上的全女性社会,其高度发达的生命技术和逻辑缜密的世界观设定令读者叹为观止。
如果没有这么多优秀的女性前辈,如果大多数人不知道她们的存在,下一代女性又会如何认知自己学习科学或写作的能力?正如乔安娜所写:“榜样缺失的后果是,如果没有成功的前辈,我们凭什么认为自己现在就会成功?如果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
让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爱丽丝·谢尔登。二战期间,她在美国军队担任情报分析员。1952年,她加入中情局,后来回到大学,于1967年获得实验心理学博士学位。她使用小詹姆斯·提普垂这个笔名,部分出于工作保密的需要,但也是因为“在我的生活中,有太多次成为某职业第一个女性的经历”。尽管作品有着明显的女性主义倾向,但在其身份公开前,评论家将小詹姆斯·提普垂比作海明威,称赞“他”有男子气概。爱丽丝·谢尔登本人对此评论道:“男性抢占了如此多的经验领域,以至于当你书写普遍主题时,你就是‘像男人一样写作’。”值得一提的是,自1992年起,在科幻作家帕特·墨菲和凯伦·乔·富勒的推动下,小詹姆斯·提普垂奖设立,并每年在世界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大会(WisCon)上颁发,以表彰那些突破了传统性别观念的幻想作品。
正如慕明在短篇集《宛转环》的序言中所说:“和园艺、编程、科幻小说等等许多曾由女性开创或主导,但之后女性被排斥、被抑制、被遮蔽的领域一样,经过艰苦、漫长的工作和等待,发明技艺的母亲终于获得承认,讲故事的磁带取回了属于‘她’的代称。”
女作家、科学家、科幻作家,如她们笔下的造物一般,于偏见里生长,在不可能中诞生。正是无数女性的坚持不懈,为后来者逐渐铺平了道路。
二、她们为何选择科幻乌托邦
说着“女性要独立、要自信”这些大道理,仅仅鼓励女性靠自己努力,就足够了吗?并非如此。
2025年6月12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5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报告显示全球性别差距已经缩小至68.8%,按照这一速度,实现完全的性别平等仍需123年。
许多人或许还记得2017年兴起的“MeToo”运动。性骚扰、性侵犯之所以频繁发生,是因为社会文化默认男性可以“拥有”和“使用”女性的身体,而她本人的意愿不受重视。
为什么女性总是被物化、被工具化?
我们与性别平等的距离,为何如此难以消除?
早在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就在《第二性》中一语道破了女性的次等地位:“在法文中,往往会以le sexe这个字来代称女人,这意味着她在男人眼中是个‘带着性别的人’。”这部皇皇巨著涉及学科之广,鲜有作品能匹敌。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到历史唯物论、文学、宗教,在主要由男人制定的规则、创造的知识以及文化中,波伏瓦剖出使女性沦为“第二性”的根源:问题在于女性总是为家庭所困。《2025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也指出,女性选择职业中断的可能性比男性高55.2%,原因主要是为了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
“因为女性有子宫,所以所有女性都应该相夫教子”,这样的逻辑听起来荒谬,却仍然是相当普遍的社会认知。波伏瓦认为,“母性”与“女性”一样,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天规训形成的。女性天然的生理特点,并不理所当然地等同于她们都有责任和能力承担社会意义上的母职。“母职往往把女性变成名副其实的奴隶,把她们禁锢在家中。因此,必须停止这种母职实践,即传统的男女分工。”
传统的男女分工,即“男主外,女主内”。操持家务、生育和照料孩子,被认为只是女性的分内之事。马克思的搭档、男性思想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一个著名论断:“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
而当进入21世纪,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支持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工作中的性别平等近在眼前,向女性开放的职业也比从前更多,为什么收入差异依然存在?假如女人想和男人一样,同时拥有婚姻、孩子和事业,会面临什么?
202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做了系统的研究。在其著作《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历程》中,她追踪了四代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之间的选择及其后果。
具体而言,刚刚大学毕业的男性与女性工资接近,毕业约10年后,二者的收入差异逐渐变得明显。克劳迪娅发现,这一变化通常始于孩子出生的一两年后,并且生育几乎总是对女性的职业生涯造成负面影响。
克劳迪娅指出,女性要在事业和家庭幸福之间谋取平衡,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时间冲突。对女性而言,所谓的黄金生育年龄,同样是发展事业的黄金时期。然而在一个家庭中,如果要赚取足够多的收入,就必然要有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其事业、将重心放在家庭上。而这个人往往是女性。即使有工作,她们休哺乳假、产假、育儿假,随时响应孩子的需求,也会影响晋升与收入。
自然,夫妻双方各有损失:男人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女人放弃了部分事业。但请注意,工作永远更有利于一个人独立谋生,而母职只关乎无私奉献,无关自我和创作。更何况,妇女承担了世界上75%的无偿照护工作(包括对幼儿和老人的),据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估计,这相当于每年为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贡献10万亿美元。
而如果一位女性想要在家工作呢?传记作家茱莉•菲利普斯撰写的《逃生梯上的婴儿》一书,记录了许多女作家在创作与育儿之间的挣扎:一旦生育,女性很难获得和男性一样不受打扰的纯粹的创作环境。孩子会没完没了地打搅她们,有人为了专心,将自己关起来或是把孩子放在逃生梯上,又要因“我不是好母亲”而时刻遭受他人谴责与自责的煎熬。而厄休拉·勒古恩之所以能一边育儿一边写作,部分是因为她的丈夫一定程度上分担了照顾孩子的任务。她回忆:“没谁能做两份全职工作:写作是一份全职工作,照顾孩子也是。但两个人可以做三份全职工作。”即便如此,在意外怀上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厄休拉仍然陷入了严重的抑郁。
综上所述,女性面临的困境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如果忽视这一点,只一味将女性独立的责任归到她们自己头上,则有失公允。
在厄休拉刚刚开始写作的年代,大部分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男性,所以她也自然而然地写男性的故事。后来,她从奇幻转向科幻,逐渐发现自己无法以男性视角写下去了。“如果我没有度过这个阶段,没有从我自己身为女性的经验中学习如何写作,我可能就停止写作了。”
身为女性的经验,恰恰是女性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出版的《看不见的女性》(中译本于2022年出版)以详实的数据,展现了女性在各个领域遭受的显性与隐性的歧视。在书中,有三个主题反复出现:女性的身体、女性的无偿看护和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它们组成了无数女性难以名状、又无可代替的生命体验。
女性主义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平等、包容的社会,这本身就是一种颠覆性的、乌托邦式的开拓。正如《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一书援引1980年《未来女性:批评文选》(Future Females: A Critical Anthology)中的预测:“科幻小说将形成当代女性主义思潮中的一个主要趋向。”许多女作家在科幻小说中找到了表达的出口。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女性科幻作家往往不约而同地书写相似的主题:能帮助女性摆脱生育之苦的人造子宫、实现孤雌生殖的全女社会、社会共同分担责任的育儿制度、性别关系与当下不同的世界……她们用笔尖戳破覆盖在痛苦之上的名为“伟大”的虚无滤镜,在现实的壁垒上凿出缝隙,让希望的光透进来,点明“从来如此”的不合理性。
非裔美籍作家奥克塔维娅·巴特勒开创了非洲未来主义这一流派,她也是第一位出版作品的黑人女性科幻作家。在她开始写作的时代,科幻领域几乎只属于白人男性,黑人女性则深陷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困境。奥克塔维娅的姥姥曾在种植园为白人做活,那里没有接收黑人儿童的学校,是姥姥教会了她母亲识字和写作。母亲丧偶后独自抚养她长大,帮助她发现了阅读这一爱好。青春期时,奥克塔维娅因外貌而被霸凌,她一度想要消失,却悲伤地发现自己“长高了六英尺”。
好在奥克塔维娅不曾真正消失。1999年,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未接受作为黑人的我隐形或不存在。身为女性和非裔美国人,我把自己写进了这个世界。我把自己写进了现在、未来和过去。”
她的短篇小说《血孩子》同时涉及种族与性别议题,讲述一个外星物种入侵后,把男人的身体当作孵卵工具的恐怖故事。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于马蝇,这种昆虫会在其他生物的伤口里产卵。奥克塔维娅受此启发而描写的男性“怀孕”场面堪称惊悚,却也因其“写实”让许多女读者感到了共鸣。在故事中,男主人公选择怀孕,不是因为好胜心,也不是被逼无奈,他只是像现实中的大多数女性一样,爱上了一个“人”,从此仰仗对方的承诺而生活。外星种族说:“我还没见过哪个人族目睹了整个诞育过程还能心平气和……应该保护好人族,免得他们看见这些。”在现实中,人类也以相同的理由蒙住年轻女性的双眼,对生育损伤避而不谈。奥克塔维娅在后记中写道:“我一直想要探讨,当男性处于绝不可能的位置上时会是什么感觉。”
目睹过去与现在的种种,新一代的女作家同样发现自己不得不写作。
韩国科幻作家金草叶考上化学系研究生后,发现比成为女科学家更难的是坚持下去。工作过劳、同工不同酬、育儿与事业的冲突阻碍着许多女性追梦。此外,韩国近年来曝光了不少针对女性的犯罪事件,在金草叶看来,这“让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不能再这么活着了’”。
于是,她转向了科幻写作。在其短篇小说《馆内遗失》中,人们可以在图书馆再现去世亲人的“思维”。刚刚怀孕的智敏想要再见一次生前曾患过产后抑郁的母亲,却发现母亲删除了自己的索引,消失了。唤醒母亲的唯一方法是找到她的遗物,但她竟然没有留下任何有意义的痕迹。“她那么生活过,又那么离开了,现在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最后,智敏得知,母亲曾在出版社工作,休产假时被裁员。“反正有了孩子,也要暂停工作。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以母亲设计的图书封面为索引,智敏终于找回了妈妈。
对数不清的女性作家而言,科幻小说是女性主义的实验室。她们可以讽刺当下,而不必担心过于针砭时弊;她们可以改写规则,推演出合乎逻辑的新型权力关系,让隐形的压迫显形。
值得强调的是,许多女性主义者不仅仅倡导解放女性,同样也支持男性从传统男子气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说:“要求女性驯服的观点,反过来也会作用于男性……男性屈从于上位者的权势,以换取刹那的欢愉。”由此推断,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也将会是各类社会成员更加平等的社会。
“世界可以是别的样子”——这是她们无法停止写作的最好理由。
三、为什么科幻需要女性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记录了一桩旧闻:乔治城大学的一位教授把她的文学课命名为“白人男性作家”,因此上了报纸头条。
长久以来,男性的经验、男性的视角被视为普适的、主流的、宏大的,而当任何创作冠以“女性”的前缀,就变成了小众的、微不足道的。然而,女性占据一半人口,没有女性视角的世界才是不完整的。存在于各个领域的性别偏见,深深影响着所有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早在1936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就在《三个旧金币》中直言:“科学也不是没有性别的。科学是男人,是父亲。”在女权运动从第二波向第三波过渡的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知识本身是否就带有性别偏见?所谓客观的立场是否仅仅是男性的立场?
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学者进入科技领域,批判其中的男性思维霸权,并开始寻找基于女性主义的技术文化。
以生物学为例,英国动物学家露西·库克在《“她”的力量》中揭示:男性视角的生物学常将性别刻板印象套用在动物身上,许多研究者只关注支持雌性被动特征的证据,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想出越来越曲折的借口,来揭示偏离标准刻板印象的雌性行为”。露西写道:“性别歧视的谬论被糅进了生物学,还扭曲了我们对雌性动物的认知……无论从什么角度讲,都不能说所有的动物社会均由雄性主导。多个不同的动物类群中都演化出了‘阿尔法雌性’(处于领导位置的雌性)。”
至于男性科幻作家笔下的女性角色,往往和其他领域大多数的男作家并无不同——大多个性单薄,缺乏能动性,主要扮演等着被爱、被拯救的性感台灯。正如厄休拉·勒古恩在《美国科幻及其他》中所写:“妇女运动让我们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了一个事实:科幻要么完全无视女人,要么便把她们描写成尖叫的布娃娃,随时随地遭受着怪物的强暴,或是因过度发育的智力器官而丧失了性能力的老处女型女科学家,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才华横溢的主人公身边忠诚的年轻妻子或情妇。”
同时,在大多数男性作家笔下,即便是再遥远的未来社会,女性仍从属于男性;他们对性别关系的设想极少脱离当下现实的框架。男作家、批评家金斯利·艾米斯在《地狱新地图》(New Maps of Hell)中指出:“承认科幻作家显然对现有的性别状况感到满意或许违背常识,但是事实的确如此”。乔安娜·拉斯也和《在世界机器的夹缝中:女性主义与科幻》(In the Chinks of the World Machine: Feminism and Science Fiction)的作者莎拉·勒法努持有相同看法:最优秀的科幻作品持有怀疑一切的理性态度,所以科幻作家尤其不应该“囫囵吞下”传统。
因此我们可以说,父权制基于男性天然比女性更优越的信念,而女性主义建立在对父权世界“自然性”的怀疑之上。正是科幻小说,为女作家们提供了谈论政治、实践女性主义的最佳空间。
任何领域都需要女性,科幻也不例外。《看不见的女性》援引的研究显示,女记者、女作家更有可能以女性视角为中心,并引用女性的观点。例如,2015年,69%的美国女性传记作家撰写关于女性主题的作品,而男性传记作家的这一比例仅为6%。
那么,女性视角为科幻创作带来了什么?既有更丰富立体的女性角色,也有对人类社会深刻的洞察和反思。在科幻中,她们能够谈论身为女性的感受,展露女性被隐藏的野心,想象一种平等或是对女性有利的社会,在未来世界打造属于她们的规则。
厄休拉·勒古恩在《黑暗的左手》中创造了格森星。这颗星球上的人平时没有固定的性别,在每月的特殊日子会分化为男性和女性。她的中篇小说《塞格里纪事》更是大胆想象了女性将男性“保护”起来的性转世界——男性拥有不必工作的“特权”,女性则拥有治理社会的权力。
厄休拉设想的超时空通讯“安塞波”早于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的发明,男作家奥森·卡德在《安德的游戏》中沿用了这一设定。厄休拉的作品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她常常探讨政治、社会如何与技术共生,形成一种综合性的科学想象。厄休拉对道家思想也颇有研究,倾向于“道法自然”而不以人类为中心。结合阴阳概念,她提出,少数精英自上而下设计的传统乌托邦是男性气质的“阳的乌托邦”,而我们要去寻找“阴的乌托邦”。1
百年以来,女作家们打造了许多个只有女性存在的乌托邦。她们往往用男性闯入者的视角或是平行世界来与纯女社会的美好形成对比,且不是简单的性转,而是保留了两性的生理差异。翻阅这些作品,你会惊讶于她们的超前与锐利。
夏洛特·吉尔曼《她的国》里,由女性组成的国家热爱和平、没有战争,这里的女人不会害羞、不会示弱,自主选择是否成为母亲,共同分担照料幼儿的责任。三位男性闯入此地,对她们既恐惧又轻蔑。小说以讽刺的笔调,嘲笑了他们的征服欲。
小詹姆斯·提普垂的《休斯顿,休斯顿,你听到了吗?》(Houston, Houston, Do You Read?)则更像《她的国》的太空版,但这次男性闯入者没能和女人谈上恋爱,反倒因暴力而自取灭亡。
乔安娜·拉斯的《雌性男人》(The Female Man)想象了四个平行时空产生交集:20世纪70年代的现实世界、男女社会割裂和互相交战的世界、女性受极端压迫的世界和只有女性的世界。小说充满了女性对困境的控诉,也展现了她们重建自我的力量。
反乌托邦小说也是女性主义科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品通过构想极端糟糕的未来,揭露性别不平等的弊端,也批判殖民、种族歧视、西方中心主义。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表示:“大多数反乌托邦作品都出自男作家之手,观点也是基于男性的视角。”因此,她创作了《使女的故事》,想象了一个女性地位极其低下的反乌托邦社会:环境污染导致人口骤降,“基列国”尚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沦为生育工具。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现实中部分地区的女性权益倒退几乎与小说里的描写无异。2019年,玛格丽特又出版了饱含希望的续作《证言》,三位女性暗中互助,最终揭露了基列国的恶行。书中,最触动读者的人物大概要数莉迪亚嬷嬷,她游走于男性掌权者之间,人物形象复杂且充满张力。
玛格丽特重视文科。她说:“科学是关乎知识的,小说则关乎感觉。”科学是工具,如何运用科学,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更是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问题。“技术创造能力源自我们的情感,而不仅仅源自我们的头脑。”
在环境恶劣的未来社会,女性仍顽强地反抗着压迫。苏赛特·埃尔金(Suzette Haden Elgin)的《母语》(Native Tongue)中,在2205年的美国,女性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沦为男性的附属品,但一群女性创造了一种秘密语言,能够表达男性中心的语言所不具备的情感和经历,以此组织反抗。
女作家同样在深入思考和书写身体。因为拥有子宫,女性需要经历男性无法体验的月经与生产,这使得女性与自己身体的联系天然比男性更紧密。珍妮特·温特森在《人形爱情故事》中,使用了时空交错叙事,探讨爱情与身体的关系;新加坡作家杨雅君(Neon Yang)则在《天堂的黑潮》(The Black Tides of Heaven)中探讨了性别认同和酷儿的亲密关系。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作家开始以女性为主角,讲述不限于性别关系主题的科幻故事,笔触同样带有温和的女本位视角,包含细腻的情感体验。
多和田叶子在《献灯使》中想象了核灾难之后的日本社会,年轻人变得孱弱、老年人却不会死去,于是老年人担任起照护的责任。同时,仿佛是对选择性堕女胎的惩罚,人类产生变异,每个人在一生中会经历一两次性别转换。小说对残疾与照护问题,以及家庭伦理的探讨,都具有女性独特的视角。
又如,韩语有省略主语和代词的习惯,如非特别提及,读者往往默认角色是男性。但金草叶的短篇集《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中,七个故事的主角都是女性。她说:“我一直对故事中缺乏女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视角感到失望,所以试图在作品中弥补这一点。”中国作家顾适也意识到:“如果我自己不写女性,男性也不会写女性;如果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的科幻作品里都没有中国文化,别的人说不定只会把中国文化作为一种东方主义奇观。”她的短篇集《2181序曲》描绘了多位“罩得住人”的女性角色,其中《魔镜算法》还刻画了一个骂骂咧咧、不尊重女性的大爷,引起很多有相似经历的读者共鸣。慕明(《宛转环》)、东心爰(《卞和与玉》)等作家,也都刻画过勇敢坚定探索科学的女性角色。
不过,在作家兼科幻评论家格温妮丝·琼斯(Gwyneth Jones)看来,女性科幻并不必然等同于女性主义科幻。前者更温和地呈现女性个体的强大,后者则更倾向于深入探究社会关系。
正如女性主义是一场包罗万象的盛宴(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阿迪契语),以女性为中心的科幻也可以多种多样。女性主义从来不是性别战争,而是对人人平等的倡议。女性视角补全了人类生命体验,丰富了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女性写作不应是科幻文学的“分支”,而是重构未来不可或缺的力量。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科幻领域,我们看到了无限可能。多读一读女作家的作品吧,或是勇敢地拿起笔去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推动变革的一部分。
- 厄休拉·勒古恩同时是《道德经》英文版译者。——编者注 ↩︎
参考资料:
- 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序言
- 乔安娜·拉斯:《如何抑止女性写作》
- 珍妮特·温特森:《十二字节》
- 丽塔·考威尔:《她的实验室》
- 西蒙娜·德·波伏瓦:《波伏瓦访谈录》
-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
- 卡罗琳·佩雷斯:《看不见的女性》
- 茱莉·菲利普斯:《逃生梯上的婴儿:创造力与母性的两难》
- 奥克塔维娅·E.巴特勒:《血孩子》
-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书写科幻传奇》
- 戴雪红:《科学、技术与性别的博弈:论唐娜·哈拉维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当代价值》
- 中国作家网:《西方科幻文学发展:悠长的回声》
- 博主慧敏:《百名女性科幻作家与她们的作品》
- SME科技故事:《手算飞船轨道的天才非裔女数学家逝世,是NASA背后隐藏英雄》
- Joan Slonczewski: Really Far Out
- The Woman Behind James Tiptree, Jr.
- The Spectacular Life of Octavia Butler
- NOWNESS现在:《韩国科幻潮,与它背后的女性引力》
- 科幻百科:《科幻主题之女性主义》
- 惊奇电台:《想象一个世界,女性拥有所有权利》
- In her 1984 science fiction novel Native Tongue, linguist Suzette Haden Elgin created a feminist language from scratch
- 后浪研究所:《当一位科幻作家放弃了让男人当主角》